我是一个智力只有三岁的色盲。
但我结了婚,还生了一儿一女。
在丈夫家,我吃馊饭,睡牛棚,穿破布。
比儿子捡来的小土狗还要卑贱。
不过因为我智商低下,这一些我都忍受得十分轻易。
本以为这样的生活会持续到我死。
可四十岁那年,我忽然清醒了。
1
那天,我正在做饭。
儿子捡的那条名叫毛毛的狗,趁我不注意,扒上灶台。
把我备着用来做菜的一条肉叼走吃了。
我吓得拿起扫把大叫着去追,要毛毛吐出来。
如果这条肉被它吃了,我肯定要得一顿好打。
但是狗眼看人低,毛毛感受得出来,我在家里的地位不如它。
毕竟它的狗窝都是封闭加毛绒内里,被允许放进内屋的。
而我,我只能住在四面漏风的牛棚,和牛挤着取暖。
我的扫把落到它身上恐吓,却不敢真正地打。
因为我知道。
狗要是被打坏了,我也会得一顿好打。
毛毛嘴里的肉眼见着一点一点地被它吞吃干净。
婆婆带着小叔子一家去县城拜佛,家里只有我一个人。
我求助无门,只能疯了似的挥舞扫把,大吼大叫。
可是没有用。
毛毛已经吃完了肉,优哉游哉地坐在那舔着嘴巴。
我想到要挨打,抖得像筛糠,发出的叫声都零零碎碎的。
我徒劳地拿着扫把追在毛毛身后,哭骂道。
「吐出来,吐,出来。」
「毛毛,给我,吐,出来。」
「求求你,吐出来。」
我的丈夫牵着我儿子回来时,看见的就是我举着扫把打狗的场面。
儿子面庞一红,嚎叫着冲上来,一把推倒我。
护犊子似的将狗护在身后。
「不准打我的狗。」
「不然我要你好看!」
我打着哆嗦,分不清是冻的还是吓的,嗫嚅着说。
「没,没打。」
「小宝,妈妈没打。」
儿子根本不听我的,身子一扭,专心去检查毛毛有没有受伤。
那边的王建二话不说,将皮带「咔咔」抽了出来,凌空划出一道劲风,紧密的皮革就狠狠地嵌到我身上。
一下又一下,像过往无数次发生过的那样,打得我满地打滚,呜哇乱叫。
正是冬天,我穿得单薄,一身皮肉都被冻紧了。
皮带抽着灼痛又生疼,磨得我本就迷糊的脑子几乎成了一团糨糊。
王建边打边骂。
「老子在外面辛辛苦苦上一天班。」
「回来连口热饭都吃不上吗?」
「我看你真是懒得出奇,皮痒了。」
「你个赔钱货一天天到底在家里干什么?」
「老子养你是要你吃白饭的?」
我涕泪横流,两只手捂完这里又捂那里,最后哪里都没捂住。
疼得我直恶心咳嗽,受不了了,才用匮乏的语言辩解。
「没有懒。」
「毛毛,把肉吃了。」
「饭做不成。」
「我没有懒。」
「肉给狗吃了?」
王建把眼怒睁,重复一遍,手里的动作更狠了,皮带像淬毒似的,打得我痛得要死了。
「你是猪?」
「连条狗都能把你欺负了?」
「你四十岁的人,弄个狗你都看不住!」
我叫得很惨,往来邻居却没有劝的。
王建的名声在村里出离得差,没有人想惹他。
儿子也略有些吓到了,小脸拧巴着看了半天,还是像从前一样,抱着狗回屋躲着。
我又是哭又是求,却很清楚。
没有人救我,只有等王建打够了停下来。
王建或许是在外面受了气,这次打了很久都没停。
我的意识逐渐模糊。
迷蒙的视线里,仿佛看见,三岁那年,在我指尖逗留的一只花蝴蝶。
那蝴蝶,可漂亮了。
是我四十年的生命里,最明亮的一点颜色。
那是我妈妈给我引来的。
2
我被王建打得昏睡了六天六夜。
第七天一早,我醒来了。
睁开眼发现,我躺在女儿出嫁前住的偏屋里。
这是我从未涉足过的地方。
可惜这间屋子并不暖和,处处都很陈旧。
我的女儿不声不响地住了十八年。
屋里围了许多人。
王建,婆婆,小叔子一家,还有别的王家亲戚。
但我第一眼看到的,是被嫁到邻省难得回来的女儿。
她坐在床边哭哭啼啼地看着我。
或许没人知道,女儿是我嫁过来后唯一的安慰。
她是我亲手养大的,事事亲为。
不像儿子,生下来就被婆婆抢走,除了喂奶不准我碰。
且这个家里,只有女儿会偷偷摸摸地对我好。
我吃力地摸摸她粗糙的手。
「宝宝,不哭。」
一屋子人都被我的声音吓了一跳。
女儿脸上挂着泪,痴痴地看着我,悲恸地扑到我怀里。
「妈,吓死我了。」
「我还以为你······」
我摩挲着她瘦弱的背脊,说我没事。
女儿的脊椎分明地顶着她微薄的皮肤。
我思绪走向了一个不曾到过的地方,莫名地问她。
「宝宝,你是不是过得不好?」
女儿听见就愣了,我也愣了。
这是以往逢年节,王建带我翻过重山回娘家讨钱花时,妈妈会问我的话。
每次她都要锲而不舍、翻来覆去地问好几遍。
我其实不懂这句话的意思。
只觉得见了母亲很高兴,傻乎乎地冲她笑,从没回答过。
但如今的我竟然,会在看到女儿手上深浅不一的暗色斑块时。
用同样的话问询她。
这不是一个智力只有三岁的傻子会有的思维。
我意识到什么,沉默地抱紧了女儿。
女儿也沉默着,没有回答。
角落里的王建不合时宜地挤进来,叼着烟,满脸不耐烦。
他叫我既然醒了,就赶紧起来做饭,不要偷闲。
我掀起眼皮看着他那张坑坑洼洼的脸,拒绝道。
「我不要。」
「我为什么要给打我的人做饭?」
在场的人都是一惊。
我嫁给王建几十年,一直逆来顺受,战战兢兢。
哪敢讲这种话。
这是我人生第一次。
各路亲戚交头接耳,说王建怕不是把我打疯了。
王建被我拂了面子,脸上五颜六色,沾满烟臭的大手不由分说地越过众人,扯住我的领子要拽我下床。
「你要翻天了呐。」
「快给老子去做饭,这么多人都等着你。」
我顺着他的力道下床站直,忽地两手用力将他一推,一下子将他推到地上发蒙地坐着。
寻常女人不会有这么大的力气。
除非她像我一样,一个人数十年如一日地操持几亩田,种完地又要去背柴砍柴,收拾了柴火还要给七八口人做饭、洗衣。
牛圈的粪也是我每天铲了背走的,一次几十斤。
这些事做几十年,力气自然大过男人。
不过来王家之前,这些事我是一点都做不来的。
他们硬要我做,不会就打。
打着打着就会了,但是会做了也要挨打。
没有别的原因,就因为我是个傻子,我的娘家又在重山之外。
我不知愁,不知苦,就算痛都记不了多久。
就这么一天天地过,到现在我四十岁。
不出意外的话,这种日子会持续到我稀里糊涂死去的那一天。
大概是老天爷看不下去。
看不下去一个男人,因为一条被狗吃了的瘦肉,要将一个女人打死。
它慈悲地拨弄了命运的齿轮。
让王建这一顿毒打,虽然打走了我半条命。
却也把我的神志打回来了。
我居高临下地看着王建。
灰暗的世界里,王建在我眼里居然是血红的。
我一字一顿地告诉他。
「我不会再给你们王家,做任何一件事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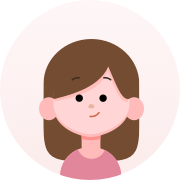






 扫码下载 精彩抢先
扫码下载 精彩抢先
 或微信搜索:猫九来啦
或微信搜索:猫九来啦
